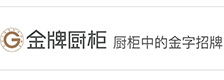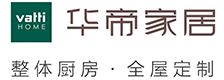CIVRO系统门窗携手IDF“建筑主义+”|林琮然、刘津瑞与你说说建筑、室内设计的那些事儿
CIVRO系统门窗携手IDF“建筑主义+”|林琮然、刘津瑞与你说说建筑、室内设计的那些事儿。
2018-06-19
IDF “建筑主义+”巡回论坛上海站访谈回顾
“+”意味着添加,融合,代表着无限可能,“互联网+”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的无限潜能,那么当建筑主义融入室内、时尚、艺术……,“建筑主义+”又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惊喜与火花?IDF“建筑主义+”2018年度巡回论坛上海站,于6月11日圆满结束。就人居环境与空间设计的关系,台湾省著名青年建筑师林琮然与85后新锐建筑师刘津瑞接受专访,分享了他们不同的建筑主义观。
林琮然 | 呈现的是作品,未呈现的是故事
Q:这次论坛的研讨主题是建筑主义+,您本身是学建筑出身的,对这个主题有什么诠释?
A:我觉得每一位建筑师或者设计师都要记得一个观念,这样做设计才能有方法、有条理的进行,这个观念很可能会陪伴你一辈子。比如说,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,都会把曾经的经验、想法或思路,进行梳理,设计也是一样,是叠加的过程,每次完成作品都需要总结,那么进行下一项设计工作时,就会从之前的作品中提取一些有用的资讯,一步步形成属于自己的闭环。近期我们一直在谈“情归自然”,我把这个当成是一直在追寻的设计方法论。
Q:您作为一名著名的建筑师,时常也会做一些跨界设计,如室内设计、产品设计、装置设计,能分享一下您触及这些领域后的感悟吗?
A:通常我们很喜欢用一个行业或者专业去看一个人,但设计恰恰不是这样的,从工业革命开始,在欧洲或者西方国家,建筑师被赋予比较大的责任,对城市美学、人们的生活、美的定义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,为什么?因为他的权限会较大,可以涉及各种领域,很多欧洲的建筑师,可以跨领域做不同的设计。而中国的设计领域分的比较细,细分之后各领域没有太多的交集,反而会产生一些矛盾,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恰恰好需要一些整合,变成一个设计系统,这个系统可以将好的理念一以贯之。在古代,君子基本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,依靠的是他思想上的一种力量和凝聚,当理念和思想可以形成一个凝固点,那么,无论在哪一个领域,都可以产出不同的东西,发挥更大的能量,这是我想要追求的。
Q:您作为心+学设的成员之一,前段时间,心+设计学设与交大共同出版了《未竟之地》,分享了未实施的项目作为大学专业教材,能具体聊一下吗?
A:《未竟之地》是在2017年中国室内设计周暨上海国际室内设计节上提出来的,这个名称是跟心+设计学设社长杜老师一起想出来的,我们想象每一位建筑师或设计师内心都有一块处女地,那块美丽的地是他想要去完成而没有完成的作品,但不能说这些作品没有价值,因为在作品呈现的那一刹那,我们看到是它最好的当下,可是也不要忘记它累积了多少次失败的过程。我们希望大家知道,所有东西的背后是很多不同故事的凝聚,这些故事虽然没有完成,但它也是一种享受的过程。设计师的生涯并不只是一瞬间,而是漫长的等待、期待和坚持的过程,《未竟之地》就是想要表达这些。在交大新书发表会上,我说了一个故事,一个美国著名的音乐家,去德国科隆演奏,演奏开始前发现钢琴坏了,他起初不愿意再上台演奏,可最后还是决定上台,那首现场收录的音乐是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曲目,也是畅销曲,所以我想说的是,所有的建筑师都会遇到挫折,但是最后呈现的部分才是最好的结果。其实,在进行CIVRO希洛门窗上海营销总部这个项目时,过程也非常曲折,这个项目在物业、结构、光线等方面,还有很多未竟的故事,所以对我来说它并不是完成片,因为跟我心中的完成片还是有距离的。
Q:内地的高考刚刚结束,对于想要报考建筑或者设计专业的学子,您有什么建议吗?
A:《建筑师的20岁》我推荐想学习建筑的学弟学妹看,里面讲了建筑师们在20岁的时候,因为想要念建筑系做了哪些事情,以及为什么他们决定成为一名建筑师,另外,希望学子们在了解想要念的科系之外,也能感受一下学校的氛围,如果你喜欢建筑系的氛围,又很喜欢同济大学的话,就应该去学校体验一下,想象自己在这所学校上课的状态。可以多接触一些建筑师或设计师,对这个领域有一些认知。
刘津瑞 | 建筑改变城市 设计改善生活
Q:本届IDF探讨的主题是“建筑主义+”,您对于这个主题是如何理解的?
A:说到建筑主义就很难避开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,前段时间我和partners出了一本书,探讨上海的新建筑,里面会有对于主义、建筑学,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一些思考。整个建筑学行业,都有一点点的焦虑,因为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冲击,所以大家会疑问这个行业的未来在哪里?其实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可能会和现在有些不同,就像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卡斯特说的,我们现在所处的空间很多都是场所空间。但之后可能会分化成两类,一类叫做流的空间,一类叫做场所空间,流的空间与流动空间是两个概念,以虹桥的枢纽为例,它是集合了交通、商业、办公、居住为一体的区域,它领先的地方在于虹桥枢纽有了新的突破,它是目前为止体量最大、规划最合理的的区域。流的空间和场所空间需要分开,追求更快的速度、更快的信息交换、更高的效率。阻碍城市的信息、交通、物质、资本流动的东西,未来就要把它们独立开,交通就是为了交通,枢纽就是为了枢纽,平台就是为了平台。所以如果从主义来说,不管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,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形式展现,在未来针对流的空间和场所空间分别设计的方式,会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。
Q:您是一名建筑师,是什么契机让您触及到家装改造项目?
A:我没有做过室内设计,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,但真正令我改变的是《生活改造家》四胞胎的设计项目,接触之后发现用户的需求是很直接的,他们才是最需要设计师的。在设计的过程中,也发现做这件事情有挑战,更有一些现实的意义。很多时候建造房子,会对城市有一些改变,和一些促进性的作用,但对于个体而言,感觉并不强烈。对于一个家而言,作为一家之主,他每天都在和家人使用这个空间,当室内做了调整和改变之后,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变化,效果立竿见影,而且长远。像《生活改造家》的四胞胎家庭,家里还有一个姐姐,他们的居住空间,通过生活的习惯和模式发生变化之后,我相信对于孩子们的成长也会起到很大作用。后来,我们对这个家庭进行了一次回访,担心设计完之后他们的生活环境又恢复成原样,但是并没有,室内非常整洁,原来小朋友比较喜欢乱丢东西,现在慢慢也养成了收纳的习惯,很令人欣慰,感觉特别有价值。做了这个项目之后,我对于家的设计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,并且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,如何控制、把握尺度,如何在小空间里解决不同适用群体的习惯,这让我觉得室内设计非常有意义,所以后面也做了一些类似的尝试和探索。
Q:您刚才说室内设计更有挑战,之后会尝试其他的设计挑战吗?
A:从建筑设计到室内设计,我原来想的太简单了,觉得室内设计不会有太多的结构或者规范的东西,后来接触了才发现,并不是这样的。从上海来看,新建的房子会越来越少,我们要着眼于眼前,把原先没有那么契合现在需求的房子进行改造,变得更加宜居,这也是目前国家的趋势和战略,也符合低碳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像上海的房子,不管是作为住、公共使用还是办公,户型主要是L型、十字型、长条型的,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,我们后来就尝试了以一类户型为个案,这个户型里有哪些设计方式是可以借鉴的,这样就可以花很少的钱、很少的代价提升生活品质。我们还尝试了早教中心、办公、文化类的设计,做着做着就发现,在跟业主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帮助他们克服困难,是很令人开心的。
Q:您是一个建筑师,除了建筑之外,您也会操刀一些室内项目,但是从体量上、工业架构上、个人尺度上来说,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是不一样的,您最想挑战的是什么?
A:对我而言,我更希望处理一些与人有关的设计,设计更多时候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,就像我自己的工作室叫立木L&M,L代表着逻辑,M代表着魔力或梦想,所以很难单纯地说我喜欢大的还是小的,或者说建筑还是室内,因为在接触每一个案例的时候,我考虑更多的是谁来使用,真正的从使用者角度来考虑他需要什么,现在的矛盾是什么,怎么解决,以及除了解决问题还能给他带来哪些惊喜,生活的仪式感是我们更加在意的。不管是建筑还是室内,我觉得本质是相通的,方法虽然不一样,只是尺度在变,其实做了室内设计之后,我们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也会考虑,有些地方要为下一步留一些可能性,留一些空间,做得更加合理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