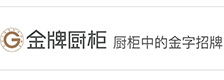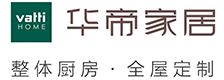厨房新文化:熬粥读书记(图)
一对一人工客服
在线解答加盟疑问
- 预约考察
- 咨询费用
- 了解区域
- 开店选址
把几本书带入厨房,傍晚,我的家务开始了。熬粥:熬紫米粥。见它沸腾,就拧出小火,熬煎多时。熬粥似熬药。粥面上浮现一层深奥的彩霞,汤汁明显加厚,我就放进淮山药,拧出大火。淮山药细细的,有灵性。盖上锅盖,待又沸腾,我就投红枣,把火拧小,慢慢地等枣香。初春天气里闻得枣香,浑身暖意。
这一锅紫米粥,一般要熬两小时,我守住灶台,几乎寸步不离。平日熬粥的时候,我会读一些旧书和新到的杂志。读旧书像遇老朋友,打个招呼就行。甚至不打招呼,点一点头,笑一笑,也行。读新到的杂志,仿佛在某些场合新认识的人,也不需要多说话,三言两语,或者一支烟一杯酒而已。
昨天有故人要我写一幅字,发来了短信,我没及时回复,就打来了电话。我怕拿毛笔正儿八经地写字,特别怕写大,要写个日记或者在书前书后写个读书随感,或者写封信,还喜欢。一想到写大字,马上会端起架子。没修到家,没修到家。就写个古人诗句吧,我想到李贺的“少年心事当拿云”。我与他少年之际就在一块儿游玩,心事肯定有,但云好像都没拿过。于是从李贺一下就想到了《唐诗三百首》。《唐诗三百首》没收录李贺的诗。今天把《唐诗三百首》翻弄一通,果然同印象里一样。蘅塘退士选编唐诗的标准是什么呢?这是我今天重新翻弄它时想知道的。主要是“诗言志”吧,开卷就是张九龄的《感遇》,可以说是蘅塘退士的命脉。还有就是唐朝之后大家对于唐诗的共识,也就是一般性见解:“丰神情韵”。孔子的“诗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,蘅塘退士基本做到了。他不选李贺,一是成见,二或许并没读过李贺的全集。不像我们现在读书这么方便。记得有位古代诗人,四五十岁了,都没机会读到多少白居易的诗,以至魂牵梦绕。李贺的《马诗二十三首》与《南园十三首》组诗,是很正宗的“诗言志”与“丰神情韵”,代表了唐诗的“主流意识”。其实李贺的“怪力乱神”之作并不多。“怪力乱神”难作,那是在天机上织锦,哪能伸手就来?
卞之琳的诗歌,近来的评价较为公正,“物有所值”。我在热气腾腾的枣香里读《卞之琳短诗选》,北塔所赠。此小册子在香港出版,中英文对照,译者就是赠者。卞之琳的诗我几乎全读过,但因为这次编排不同,似乎就有不同意味,也就有重读的兴趣。这并不玄乎。我们把客厅里的茶几沙发挪挪位置,不也就像搬了个新家而眼前一亮?卞之琳的诗,数《断章》在世俗社会里最有名。他的《距离的组织》:
想独上高楼读一遍《罗马衰亡史》,
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。
报纸落。地图开,因想起远人的嘱咐。
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。
(醒来天欲暮,无聊,一访友人吧。)
灰色的天。灰色的海。灰色的路。
哪儿了?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。
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。
好累呵!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?
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。
他自己给这首诗加了许多注,我把注去掉,看来更“一树碧无情”——幸亏李商隐没给自己的诗加注。“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”,这一句是用现代汉语写的唐诗(对“我寄愁心与明月”的“创造性模仿”。把“创造性”和“模仿”连缀,是不是搞怪?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太长,就会产生“创造性模仿”现象。中国文学史、中国绘画史、中国书法史……就是一个“创造性模仿”过程。新诗的“模仿”一直在选择、比较之中,“创造性”尚未主动,如果悲观地看来,几乎还没有过,《女神》不是,李金发不是。未来会抱着乐观态度?新诗或许是“模仿创造性”,与传统的“创造性模仿”为两种范畴)。这时,枣香顶高锅盖,越来越浓,我把火再拧小点。几期《星星》诗刊上都有当代诗人或评论家所选的新诗一百首名录,每个人都想表达自己的立场和看法,但意识或潜意识却都在一个游戏规则里:适用的知识公共遗产。那么,能有什么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呢?紫米粥终于熬好,熄火。
我想,“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”,是不是更接近杜甫的“瞑色带远客”!